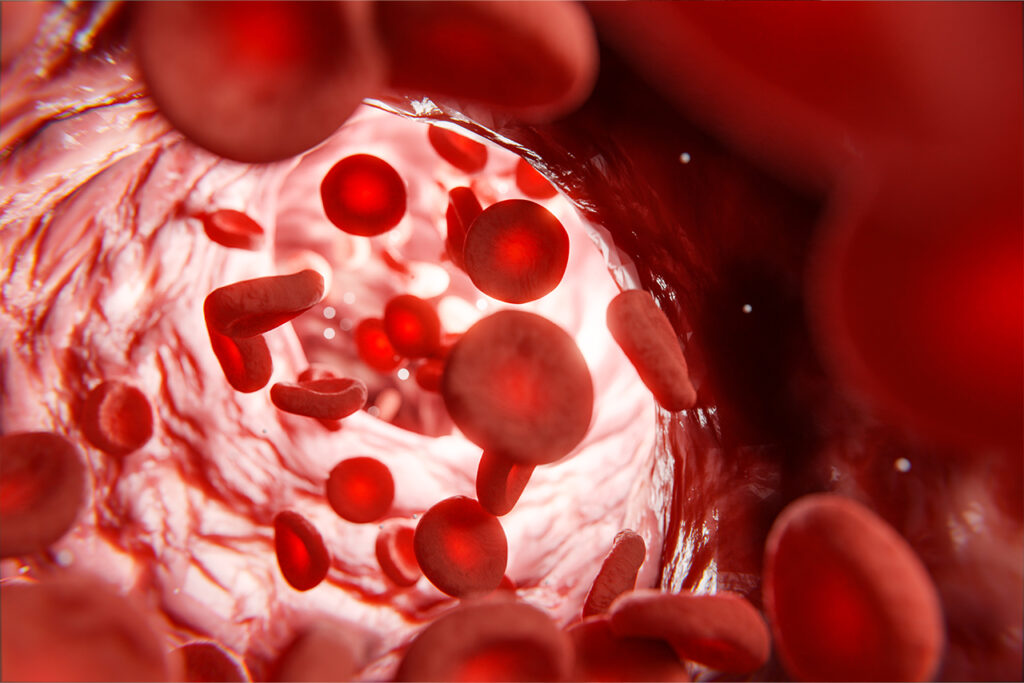還膽固醇一個清白 !
作者:馬特‧裡德利
基因組是記載著過去的瘟疫史的聖經。我們的祖先對瘧疾和痢疾的長期抗爭被記錄在人類基因的多樣性中。你有多大機會能夠避免死於瘧疾,是在你的基因裡與瘧疾病原體的基因裡事先編排好了的。你把你的隊伍送出去參加競賽,瘧原虫也把它的隊伍送出來。如果它們的進攻隊員比你的防守隊員棒,它們就贏了。抱怨你的差運氣吧,你沒有替補隊員可換。
但是,應該不是這樣的吧?基因對疾病的抵抗能力應該是我們的最後一道防線,有各種各樣比這簡單的辦法來打敗疾病的。睡在蚊帳裡面,把臭水溝抽乾,吃藥,在村子裡撒 DDT。吃好,睡好,避免精神壓力,讓你的免疫系統保持健康狀態和在多數時候保持愉快的情緒。所有這些都與你是否會染上疾病有關。基因組可不是惟一戰場。在前面幾章裡我進入了簡化論的習慣。我把生物體拆開,把基因分離開,去辨別它們每一個有什麼興趣。但是沒有一個基因是孤島。每一個都存在于一個巨大的聯盟之內,也就是身體。現下是把生物體的各部分放回到一起的時候了,現下是去探訪一個“社交很廣〞的基因的時候了。這個基因的惟一功能就是把身體裡一些不同的功能組織到一起。這個基因的存在昭示出我們有關肉體 ─ 精神的二重性是個謊言,它侵蝕著我們對人的認識。大腦、身體和基因組是被捆在一起的三個舞伴。基因組與另兩者相互控制。這多少說明了為什麼基因決定論是一個神祕的東西。人類基因的啟動與關閉可以被有意識的與下意識的外界活動所影響。
膽固醇是一個充滿危險的詞。它是心臟病的病因,是個壞東西,是紅肉,你吃了就要死的。其實,把膽固醇與毒藥等同起來的做法是錯得不能再錯了。膽固醇是身體的一個基本成分,它是在一個微妙將身體各部分組織到一起的生物化學與遺傳系統裡佔有中心位置。膽固醇是一類很小的有機物,能溶解在脂肪裡,不能溶解在水裡。身體利用來自飲食的糖類合成它所需要的大部分膽固醇,沒有它,人就活不下去。起碼有五種至關重要的激素是由膽固醇為原料所製成的,每一個都有獨特的功能︰孕酮、醛固酮、皮質醇、睪酮和雌二醇。它們總稱類固醇。這些激素與身體中的基因的關係既親密又迷人,卻也讓人不安。
類固醇激素被生命體使用了很長時間,也許比植物、動物和真菌的分道揚鑣還要早。促使昆蟲蛻皮的激素就是一種類固醇。在人類醫學裡那個被人們稱為維生素 D 的謎一般的物質也是類固醇。有些人工合成的(或說是合成代謝)類固醇可以騙身體去抑制炎症,另外一些則可以用來強化運動員的肌肉。但是還有一些類固醇,雖然是從植物中提取出來的,卻與人類的激素足夠相似,可以用做口服避孕藥。還有另外一些是化學公司的產品,也許它們要為被污染水流中雄魚雌化以及現代男人精子數目的減少負責。
在第十號染色體上有一個基因名叫 CYP17。它製造一種,使得身體能夠把膽固醇轉化成皮質醇、睪酮和雌二酮。如果沒有這個,這個轉化途徑就被堵上了,那個時候,從膽固醇就只能造出孕酮和皮質酮。沒有這個基因的正常形式的人無法製造出其他的性激素,所以他們就無法進入青春期之后的階段。如果他在基因上是男性,他也會長得像個少女。
但是先把性激素往旁邊放一放,來考慮一下用 CYP17造出的另一種激素︰皮質醇。人體內的幾乎每一個系統都用得上皮質醇,它名副其實地是一個把身體和精神結合起來的激素,因為它可以改變大腦的架構。皮質醇干預免疫系統,改變耳朵、鼻子和眼睛的靈敏度,改變各種身體機能。當你的血管裡流動著很多皮質醇的時候,你就處於壓力之下,這是壓力的定義。皮質醇與壓力幾乎就是同義詞。
壓力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一個將要來臨的考試、最近一個親人的死亡、報紙上的什麼嚇人的消息或者因為照顧一個早老性痴呆症病患而感覺到的無休止的勞累。造成短暫壓力的元素會導致腎上腺素與去甲腎上腺素的迅速上升,這兩種激素使心跳加快,雙腳冰涼。這兩種激素在緊急情況下讓身體做好“打還是跑〞的準備。造成長期壓力的元素啟動一條不同的路徑,結果是皮質醇緩慢而持續地增加。皮質醇最驚人的效應之一是它能夠抑制免疫系統的工作。那些準備一個重要考試並出現了受到心理壓力之後,特有的生理特點的人更容易得感冒或受到其他感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因為皮質醇的效應之一就是減少淋巴細胞 ─ 白細胞的活性、數量和壽命。
皮質醇靠啟動基因來做到這一點。它只啟動內含皮質醇受體的細胞裡的基因,皮質醇受體則是由其他某些開關來控制的。它啟動的那些基因的主要功能,是啟動其他一些基因,有些時候,再啟動的基因又去啟動其他的基因,如此下去。皮質醇的間接影響可以多至幾十甚至幾百個基因。但是這個過程的開端 ── 皮質醇的產生則是因為腎上腺皮質裡有一系列的基因被啟動了,它們製造出了生產皮質醇所需的,CYP17 蛋白質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讓人頭昏眼花的複雜系統︰如果我只是試著列出最基本的化學回應鏈,就能讓你悶得要哭。所以,也許這樣說就足夠了︰你需要幾百個基因來生產和調節皮質醇並對皮質醇做出適當回應,而幾乎所有這些基因的作用都是把其他基因啟動或關上。這是很適時的一課,因為人類基因組裡大部分基因的功能就是調節其他基因的表達。
我說過我不會讓你覺得悶,但還是讓我們瞟一眼皮質醇的一個效應吧。在白細胞裡,皮質醇幾乎肯定參與了啟動一個名叫 TCF 的基因,也在十號染色體上,這樣 TCF 就可以製造自己的蛋白質,然後用它去抑制一個名叫白介素二號的蛋白質的表達。白介素二號是一種使白細胞高度警惕、提防微生物的襲擊的化學物質。所以,皮質醇會抑制你的免疫白細胞的警惕性,從而使你更容易得病。
我想放在你面前的問題是︰到底誰是管事兒的呢?是誰在一開始就把這些開關都放在了合適的位置上?又是誰決定什麼時候把皮質醇釋放出來?你可以說基因是管事兒的,因為身體的分化 ── 身體內形成不同的細胞類型,在每一類型內活躍著的基因都不同 ── 歸根究底是個遺傳的過程。但是這是不確切的,因為基因並不會引起生理和心理壓力。一個所愛的人的死亡或是一個即將來臨的考試並不與基因直接對話。它們只是經過大腦處理的訊息。
那麼,大腦是管事兒的了?腦子裡的下丘腦會發出一個信號,讓腦垂體釋放一種激素,它會告訴腎上腺皮質去製造和分泌皮質醇。下丘腦則是從大腦裡有意識的那些區域接受指令,而這些區域又是從外部世界中得到訊息。
但是這也不能算是個答案,因為大腦也是身體的一部分。下丘腦之所以刺激腦垂體,腦垂體之所以刺激腎上腺皮質,並不是因為大腦認識到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大腦並沒有設立這樣一套系統,讓你在要考試的時候就容易得感冒。是自然選擇設立的這樣一個系統(原因我稍後會解釋)。而且,無論如何,這樣一個系統都是非自主、無意識的舉動,也就是說,是考試,而不是大腦,在主導這一切事件。如果考試才是罪魁禍首,那麼我們就應該怪社會了,但是社會又是什麼?也不過是很多個體的集合,於是我們就又回到身體上來了。另外 ,對抗壓力的能力也因人而異。有些人覺得即將來臨的考試非常恐怖,其他人卻一路順利。區別在什麼地方?在製造、控制皮質醇與對皮質醇做出回應這一系列事件的鏈條上,易受壓力的人與那些對壓力沒有什麼回應的人相比,肯定有一個地方在基因上有細微的差別。但是,又是誰、是什麼控制著這個基因上的差別呢?
真正的情形是,誰也不是管事兒的。讓人們習慣於這樣一個事實是太難了,但是,世界充滿了錯綜複雜的系統,它們設計巧妙,部件之間相互緊密地聯繫著,但是卻沒有一個控制中心。經濟就是這樣一個系統。有一個幻覺是如果有人去控制經濟 ── 決定什麼產品應該由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生產 ── 它就會運轉得更好。這個想法給全世界民眾的健康和富裕都帶來了巨大災難,不僅是蘇俄,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從羅馬帝國到歐洲國家聯盟的高清晰度電視計畫,由一個中心做出的應該在哪個方面投資的決定比無中心的市場調節而成的“混亂〞差遠了。所以,經濟系統不應有控制中心,它們是由分散的元素來控制的市場。
人體也是這樣。你不是一個透過釋放激素來控制身體的大腦,你也不是一個透過啟動受體來控制基因組的身體,你也不是一個透過啟動基因來啟動激素來控制大腦的基因組。你同時又是以上所有這些。
心理學裡很多最古老的說法可以概括成此類錯誤概念。支持與反對“遺傳決定論〞的理論都事先假設基因組的位置是在身體之上的。但是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是身體在需要基因的時候把它們啟動,身體之所以這樣做,常常是因為它是在對大腦(有時還是有意識的)對外部事件的回應做出回應。你可以只靠想像那些給人壓力的場景 ── 甚至是虛構的 ── 就可以提升你體內的皮質醇水準。與此相似,爭論一個人所受到的某種痛苦純粹是精神上的原因還是也有部分是生理上的原因 ── 例如 ME,或叫慢性疲勞綜合症,是完全不對的事情。大腦與身體是同一個系統的兩個部分。如果大腦在回應心理上的壓力時刺激了皮質醇的釋放,而皮質醇抑制了免疫系統的活性,從而一個潛伏在體內的病毒感染得以發作起來,或是一個新的病毒得以進入身體,那麼症狀雖然是生理上的,原因卻是心理上的。如果一種疾病影響到大腦,從而改變人的心情,那麼原因雖是生理上的,症狀卻是心理上的。
這個題目被稱做心理神經免疫學,它正在慢慢地成為時尚。抵制它的多是醫生,而把它吹得很神的是各種給人實施信心療法的人。但是,證據卻是足夠真實的。長期心情不好的護士更容易得凍瘡,雖然其他護士可能也帶有同樣的病毒。焦慮的人比起心情好的樂天派,更容易得陣發性的生殖系統疹。在西點軍校,最容易得單核細胞增多症和得了這種病之後最容易出現嚴重症狀的,是那些被功課壓力搞得焦慮不安的學生。那些照顧早老性痴呆症患者的人(這是個壓力很大的工作)的抗病 T 淋巴細胞要比估計的少。在三哩島(Three Mile Island)核設施事故【1979 年在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州附近三哩島核電站發生的核洩漏事故,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是人們一度懷疑放射性會結周遭居民的健康造成很大損害。── 譯者注】發生時居住在那附近的人,事故發生三年之後得癌症的比估計的多,並不是因為他們受到了放射線的傷害(他們並沒有),而是因為他們的皮質醇大量增加,降低了免疫系統對癌細胞的回應。那些受到配偶死亡之痛的人,之後幾個星期之內免疫力都比較低。父母如果在前一個星期裡吵過架,那麼他們的孩子就更容易得病毒感染。在過去的生活中有過心理壓力的人,比起那些一直生活愉快的人來更容易患感冒。如果你發現這些研究有點讓人難以置信,那麼我告訴你,這些研究中的大多數在老鼠身上也能夠得到相似結果。
可憐的老蕾妮‧笛卡兒(Ren Descartes)【17世紀法蘭西數學家、科學家、哲學家。── 譯者注】,人們通常說是他發明了主宰了西方世界的身心二元論,使得我們拒絕接受精神可以影響肉體、肉體也可以影響精神這樣一個觀點。把這個歸罪於他可不公平,這是我們大家都犯的錯誤。而且,不管怎樣,並不都是二元論的錯 ── 這個理論本來是說有一個存在於組成大腦的物質之外的精神。我們都犯過一個比這更大的錯誤,犯這個錯誤如此容易,我們自己都沒有察覺。我們直覺地假設身體裡的生物化學回應是因,行為是果,我們還在思考基因對我們生活的影響的時候把這個假設推到可笑的極致。如果基因對行為有影響,那麼基因就是因,就是不可變的。這個錯誤不僅遺傳決定論者會犯,他們那些吵鬧的反對者也犯,這些反對者認為行為“不是在基因裡〞,他們說行為遺傳學所暗示的宿命論和先決論讓人反感。他們給了遺傳決定論者太多餘地,沒有對“基因是因〞這個假設提出疑問,因為他們自己也做了同樣的假設︰如果基因是與行為有關的,那麼基因肯定是在金字塔的頂端。他們忘記了,基因是需要被啟動的,而外界事件 ── 或者說,由自由意志控制的行為── 可以啟動基因。我們可遠不是縮在我們那無所不能的基因腳下,受它們的恩賜,我們的基因經常是受我們的恩賜。如果你去玩“高空彈跳〞,或者找一份壓力很大的工作,或者持續地想像一個可怕的事情,你會提升你體內的皮質醇水準,而皮質醇就會在你的身體內跑來跑去地啟動各種基因。(還有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就是你可以用故意而為的微笑來刺激你大腦裡的“高興中心〞,就像你可以用一個愉快的想法來使你微笑一樣。微笑真的會讓你覺得愉快一些。生理變化可以被行為調動。)
關於行為怎樣改變基因表達,有些最好的研究是用猴子做的。很幸運的,對於那些相信進化論的人來說,自然選擇是個節省得可笑的設計師,她一旦想出了一個基因與激素的系統用來顯示和對付身體所受的壓力,她就很不情願修改了。(我們的 98%是黑猩猩,94%是狒狒,還記得吧?)所以,在我們體內與在猴子體內,有同樣的激素用同樣的方法啟動同樣的基因。在非洲東部有一群狒狒,它們血液中的皮質醇水準被人們仔細地研究過。雄狒狒到了一個特定年齡都慣於加入一個狒狒群。當一只年輕的雄狒狒剛剛加入一個狒狒群的時候,他變得極富攻擊性,因為他要透過打架來建立他在自己選擇的這個“集體〞裡的地位。他的這一行為使得他這位“客人〞的血液裡的皮質醇濃度大幅上升,他的那些不情願要他的“主人〞們血液皮質醇濃度也上升了。隨著他的皮質醇(以及睪丸酮)濃度上升,他的淋巴細胞的數量減少了,他的免疫系統直接受到了他的行為所造成的衝擊。與此同時,在他的血液裡,與高濃度脂蛋白(HDL)結合在一起的膽固醇越來越少。這樣的現象是冠狀動脈堵塞的一個經典的前兆。這個雄狒狒透過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改變自己的激素水準,於是也就改變了自己體內的基因表達,這樣,他便增加了自己受微生物的感染與得冠狀動脈疾病的機會。
在動物園裡生活的那些得冠狀動脈疾病的猴子都是在尊卑順序裡最下層的。它們被那些地位更高的同伴欺負,持續地感受到壓力,血液裡皮質醇濃度高,大腦裡缺乏 5-羥色胺,免疫系統永久性地被抑制著,它們的冠狀動脈壁上積滿了傷疤。到底這是為什麼,仍然是一個謎。很多科學家現在相信冠狀動脈疾病至少部分是由於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例如一種球狀的革蘭氏陰性細菌和疹病毒。壓力帶來的是降低免疫系統對這些潛伏的感染的監視,使得它們得以繁榮起來。在這個意義上,也許在猴子那裡心臟病是一種傳染病,雖然壓力也會有一定作用。
人和猴子很像。在尊卑次序裡靠底層的猴子容易得心臟病這一發現,是緊跟著另一個更讓人吃驚的發現之後做出的。另外一個發現是︰英國的公務員得心臟病的可能性是與他們在這個官僚機構裡的地位有多低成正比的。一個大型、長期的研究調查了 1.7 萬名在倫敦警察局工作的公務員,一個幾乎令人無法置信的結果出現了︰一個人在工作中的地位比他是否肥胖、是否吸煙和是否血壓高更能準確地預示這個人是否有心臟病。一個做低級工作的人,比如清潔工,比起一個在人堆兒上面地位穩固的秘書,得心臟病的可能高幾乎三倍。實際上,即使這個秘書很胖、有高血壓,或者吸煙,在每一年齡段他得心臟病的可能性仍然小於一個很瘦、血壓正常且不吸煙的清潔工。在 60 年代對 100 萬名貝拉電話公司雇員的一個類似調查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
把這個結論考慮一分鐘。它把別人告訴過你的所有關於心臟病的知識都給削弱了,它把膽固醇推到了故事的角落(膽固醇高是一個危險元素,但是只在那些因為遺傳原因而容易高膽固醇的人那裡才是如此,而且即使對於這些人,少吃含脂肪食物的收益也很小)。它把飲食習慣、吸煙和血壓 ── 醫學界喜歡把這三者說成是心臟病的生理原因 ── 變成了間接的致病元素。它把一個陳舊和已經不太為人所信的說法變成了一個注腳,這個說法認為壓力和心臟病來自於繁忙的職務高的工作,來自於喜歡快節奏生活的個性。這個說法有一絲真理在裡面,但不多。科學研究把這些元素的作用都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與生理狀況無關的純粹環境的元素︰你在工作中的地位。你的心臟是否健康要看你拿的薪水怎麼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猴子那裡有些線索。它們在尊卑次序裡越低,它們就越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公務員也如此。皮質醇濃度的提升不是看你面對的工作數量多還是少,而是看你被多少人呼來喝去。實際上你可以透過實驗來演示這個效果︰給兩組人同樣多的工作,但是命令一組人用一種規定的方法去做這個工作,必須遵守某個事先規定的進度。這一組被外界控制的人比起另外一個組來,體內因壓力而釋放的激素濃度更高,血壓升高,心率加快。
在對倫敦警察局雇員進行的研究開始 20 年之後,同一項研究在一個已經開始私有化的公眾服務部門裡被重複了一次。在研究一開始,公務員們都不知道失業意味著什麼。事實上,當研究者們為這項研究設計問卷的時候,被調查對象對問卷中的一道題提出了異議,這道題是問他們是否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他們解釋說,在公眾服務這個行業,這個問題根本沒有意義,他們最多會被轉到另外一個部門去。到了 1995 年,他們就清楚地知道失去工作意味著什麼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已經嘗過失業的滋味了。私有化的結果,是給了每個人這樣一種感覺︰他們的生活是受外部元素控制的。一點也不令人吃驚地,心理壓力增加了,健康情況隨之下降了,健康情況惡化的人數之多,無法用飲食、吸煙、喝酒方面習慣的改變來解釋。
心臟病是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時出現的症狀,這樣一個事實解釋了它的出現為什麼是分散的。它也能夠解釋為什麼那麼多有高級職務的人退休“享受悠閒生活〞之後不久就會得心臟病。他們常常是從指揮一個辦公室“淪落〞到在由老伴做主的家庭環境裡於一些“低級〞的需要動手的活兒(洗碗、遛狗之類)。它能夠解釋為什麼人們可以把某一種疾病甚至是心臟病的發生延遲到一個家庭成員的婚禮或是一個重大慶典之後 ── 直到他們操持、忙碌、做出決定之後。(學生也是更容易在緊張的考試之後生病,而不是在考試期間。)它能夠解釋為什麼失業和靠救濟金生活是如此有效的讓人生病的辦法。在猴群裡面,沒有一隻雄性首領是像政府的社會福利署控制那些領救濟金的人那樣來鐵面無私地控制它屬下的猴子的。它甚至有可能解釋為什麼那些窗戶不能被打開的現代化大樓會讓人容易生病,因為在老式樓房裡面人們能夠對自己的環境有更多的控制。
我要再強調一遍我已經說過的話︰行為遠不是受我們的生物特性所控制,我們的生物特性常常是受我們的行為控制的。
我們發現的皮質醇的特點對於其他類固醇激素也適用。睪丸酮在體內的水準與攻擊性成比例。但這是因為這種激素導致攻擊性,還是因為攻擊性導致這種激素的釋放?我們的唯物主義思惟使得我們發現第一種說法比較可信。但是事實上,對於狒狒的研究表明,第二種說法卻更接近於真理。心理變化先於生理變化而出現。精神驅動身體,身體驅動基因組。
睪丸酮和皮質醇一樣可以抑制免疫系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很多物種裡雄性比雌性容易染病,染病之後的死亡率也比雌性高。免疫機制的抑制不僅僅只反映在身體對於微生物的抵抗力方面,也反映在對於大的寄生蟲的抵抗力方面。牛蠅在鹿和牛的皮膚上產卵,孵出來的蛆蟲先要爬進這些動物的肉裡去,然後才返回到皮膚上去做一個小“窩〞在裡面變成蠅。挪威北部的馴鹿就特別為這種寄生蟲所困擾,但在雄鹿身上又明顯地比雌鹿身上更嚴重。平均來說,到了兩歲的時候,一只雄鹿身上牛蠅的“窩〞比雌鹿身上要多兩倍。但是,被閹割了的雄鹿身上牛蠅的“窩〞又與雌鹿差不多了。類似的模式在觀察很多寄生蟲的時候都會發現。例如,包括引起南美錐蟲病的原生動物,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病就是達爾文長期不適的原因。在智利旅行的時候,達爾文曾被傳播南美錐蟲病的蟲子叮咬過,他后來的一些症狀也與這種病相吻合。如果達爾文是個女人,他也許就用不著花那麼多時間替自己委屈了。
但是在這裡,我們從達爾文那裡得到啟發。睪丸酮抑制免疫系統的功能這一事實被自然選擇的表弟 ── 性別選擇 ── 給抓住並且很充分地利用了。在達爾文論進化的第二部著作《人類的由來》裡,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想法︰就像育鴿子的人能夠培養良種鴿子一樣,女人也可以培養“良種〞男人。如果雌性動物在連續多代裡用固定的標準來選擇與誰交配,她們就可以改變她們這個物種裡雄性的身體形狀、大小、顏色或歌聲。事實上,就像我在關於 X 和 Y 染色體的那一章裡講過的,達爾文提出過,這樣的事在孔雀裡就發生過了。在他之後一個世紀,一系列的實驗與理論研究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證明了達爾文是正確的。雄性動物的尾巴、羽毛、角、歌聲和身體大小都是由於一代一代的雌性動物在擇偶時條件一致而逐漸形成的。
但是為什麼呢?一個雌性動物選了一個長尾巴或是大聲唱歌的雄性動物,她能得到什麼可以想見的好處呢?在人們的爭論中,有兩個受人歡迎的理論占了主要位置。一個是說,雌性動物需要迎合時尚,否則她們生的兒子可能就不會被那些迎合時尚的雌性動物選中。另一種理論是我想在這裡讓讀者考慮的,那就是雄性體表那些“裝飾物〞的質量以某種模式反映了他的基因的質量,尤其是反映了他對流行疾病的抵抗力。他是在對所有願意傾聽的人說︰看我是多麼強壯啊,我能夠長一條長長的尾巴,能夠唱這麼動聽的歌,是因為我沒有得瘧疾,也沒有生寄生蟲。睪丸酮能夠抑制免疫系統這一事實其實是幫助了雄性,使他的“話〞更加真實可信。這是因為他那些“裝飾物〞的質量取決於他血液裡睪丸酮的濃度︰他體內的睪丸酮越多,他的外表就越五顏六色,身體就越大,越會唱歌,也越有攻擊性。如果他能夠在免疫機能被睪丸酮降低了的情況下不僅不生病,還能長一條大尾巴,那麼他的基因肯定很了不起。這幾乎像是免疫系統把他的基因“真相〞掩蓋住了,睪丸酮則把帷幕掀開,讓雌性直接看看他的基因到底怎麼樣。
這個理論被稱做免疫競爭力缺陷,它是否正確,取決於睪丸酮對免疫系統的抑制作用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一個雄性動物無法既提升睪丸酮的濃度又使免疫系統不受影響。如果這樣一個雄性動物存在,他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會留下許多後代。因為他既能長一條長尾巴又能有免疫力。因此,這個理論暗示著類固醇與免疫能力之間的聯繫是固定不變、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就更讓人迷惑了。沒有人能夠解釋為什麼這個聯繫一開始會存在,更別說它為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了。為什麼身體被設計成這樣,它的免疫系統要被類固醇激素抑制?這個設計意味著每當生活中的事件使你感到壓力的時候,你就更容易受微生物感染,更容易得癌症和心臟病。這簡直是在你倒地的時候上去踢你一腳。它意味著每當一個動物提升自己的睪丸酮濃度以與對手爭奪配偶或是向異性展示自己的時候,他就更容易受微生物感染,更容易得癌症和心臟病。為什麼?
不少科學家都為這個謎絞過腦汁,但是斬獲甚微。保羅‧馬丁(Paul Martin)在他關於心理神經免疫學的書《患病的意識》中,討論並否定了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說,這一切只是一個錯誤,免疫系統與對壓力的回應之間的聯繫只是另外某些系統的副產品。就像馬丁指出的,對於人體免疫系統這樣一個有著複雜的神經與化學聯繫的系統來說,這是一個相當不令人滿意的解釋。身體裡很少有哪個部分是偶然形成的、多餘的或是沒有用處的,複雜的系統更是如此。自然選擇會無情地把那些抑制免疫系統的東西砍掉,如果它們確實沒有用處。
第二種解釋是說,現代生活模式製造出的壓力很多是不自然的、過久的,在以前的環境裡這樣的壓力通常都是短暫的。這個解釋同樣令人失望。狒狒和孔雀是生活在很自然的環境裡,可是它們 ── 以及地球上幾乎所有的羽族和哺乳動物 ── 也因類固醇而遭到免疫抑制。
馬丁承認這是令人不解的事。他不能解釋壓力不可避免地抑制免疫系統這一事實。我也不能。也許,就像麥克‧戴維斯(Michael Davies)提出的那樣,免疫系統功能的降低是在半飢餓的時候 ── 在現代社會之前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生存狀態 ── 保存能量的辦法。也或許,對皮質醇的回應是對睪丸酮回應的副產物(這兩種物質在化學成分上非常相似),而免疫系統對睪丸酮的回應則可能是雌性動物的基因故意安排在雄性動物體內的一個機制,用來把那些對疾病的抵抗力更強的雄性與其他的區別開來。換句話說,類固醇與免疫系統的聯繫也許是某種性別對抗的產物,就像在 X 和 Y 染色體那一章裡討論過的一樣。
摘自:《基因組︰人種自傳23章》